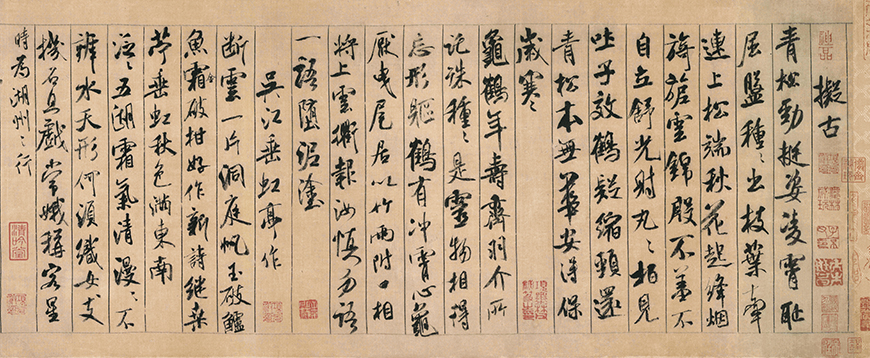第十三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嘉宾合影
2019年11月9日、10日,第十三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在广州召开。今年年会的主题是“批评视野中的艺术机构”,与以往多从批评自身出发不同,今年年会却将讨论的方向转向批评家所必须面对的艺术机构网络。


2019年11月9日,第十三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在广州召开。图为开幕现场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今年与会者们的发言,似乎格外接地气。一般而言,我们所说的艺术机构,包括博物馆、美术馆、艺术空间、画廊、博览会、专业媒体以及美术学院等等,参与年会的批评家、策展人,依赖机构网络来开展工作,并且自身就是这套艺术机制中的一环,结合自身的工作经验,对于历史和当下的艺术机构问题,他们都能提出开放和具有建设性的意见。与此同时,身处行业前沿的他们,感受到的时代变化也最为强烈。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总馆长、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王璜生最近几年一直在研究所谓的“新美术馆学”问题,其中所涉及的核心问题有三个:一是关于“人”,“新美术馆学”关注艺术家,并不局限于关注艺术家的创作成果,更关注作为艺术家的人。此外,公众作为美术馆履职和公共服务的对象,是美术馆运营的核心。二是关于多向度的“空间”,“新美术馆学”更多倡导所谓的公共空间,让空间的精神性和物理性更加开放。三是关于“制度”,美术馆的公共化意味着它将被视为独立文化议题、文化政策与理念、意识形态与全球重大问题表达、讨论甚至争论的场所空间。对“治理”和制度的认识扩大了美术馆在文化历史活动中的参与性,也加强了人们对美术馆文化功能的认识。
除此以外,随着传播媒介的变化,媒体格局也发生了变化,除了我们所熟知的专业媒体(如杂志、周刊、期刊)、机构媒体(如广州美院美术馆、故宫)、自媒体外,微博、微信、抖音等社交平台在文化传播里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志安发现,“在网络化社会中,每个人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可以一边看着杂志、一边听着音乐,同时还可以做手机的交互。看展时也是这样,身体进入美术馆,可以一边看展,一边扫二维码在线交流,还可以社群互动。”
无论是媒体还是美术馆,如果仅仅为我们提供严肃、专业的内容,观众可能已不会买账,“今天的年轻人,除了知识之外,更在意自己的体验、互动,这就要求传播者把我们认为有价值的知识,变成一种体验,变成一种服务,变成可参与的审美,甚至是一种游戏。”
中山大学视觉文化研究中心冯原认为,“所谓策展机制就是用流动型文化来扩大高峰型文化,今天我们处在文化并存的时代,很难说哪一种文化会取代某种文化,一个机构或者美术馆中,或者存在两种文化,如何衡量它们,最后结果只能说是文化在比较中产生。”
由此可见,在体制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艺术机制已发生了剧烈变化,所以今年的年会,在“批评视野中的艺术机构”这一总的主题底下,设置了三个分议题。



2019第十三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分组讨论现场/A组
A/策展:体制与民间
其中第一个就是“策展:体制与民间”,所涉及的是策展在不同类型的系统中的方式和关系。
70多岁的邓平祥把自己的一生分为两个年龄段,前30年是在体制下生存,无论是发言或者评论,哪怕是很小的文章,实际上没有人的立场,是代表组织和体制说话。改革开放以后,依据40年的个人经验,最大的成果就是要按照个人说话,按照良知说话,按照我对公共知识的理解来说话,只有这样,你才不会惧怕其它“风浪”,也不会失掉自我。 一直游离在体制与民间这两个地方之间的杨卫,对这一话题的体会比较深刻。上世纪80年代,国家自上而下进行反思,无论是民间也好,体制也好,两者握手言和,合力产生了80年代思想繁荣开放的局面。策展人掌握着与体制有直接关系的权力,如果能把这些概念澄清,有助于策展人概念的推进。 唐尧则认为“民间力量在上升,这种上升实际上从某种意义来说在威胁或者消解我们所说的体制化美术馆的机制。” 从艺术批评和策展的角度,刘礼宾并不太关注所谓民间或者官方的立场,因为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都可以策划出很学术的展览。但作为策展人,2015年之后,他开始减少或推掉策展的机会,因为当前的环境已经变得非常复杂。“策展行为和批评行为已经不在批评家身上,更多的是国与国之间文化的博弈。但当前真正有效或者具有批判意识的展览有,却并不多。” 在胡震看来,体制和民间之间,归根结底就是策展主动权和被动的概念。在官方美术馆策展,大多数情况下策展人都是被动的,要按照主办方的要求进行策划,相对来讲,民间拥有更多自主权和话语权。一个策展人和批评家,要有连续性和系统性的批评概念。 对于体制与民间的哲学化思考,李晓峰的发言非常有代表性,他认为“我们都在走向体制,但是我们都很坚守民间,再思辨一点叫做‘如何从人的体制化走向体制的人化’。”在他看来,无论是美术馆还是民间机构,越来越体制化似乎已成“宿命”,但体制与民间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我们需要一个中立灰色地带,而“学院是唯一一个中立的地方” 。 冯原的观点则更加中立和哲学化,他客观理性地分析了体制和反体制之间的张力和可能性。体制制度的形成有助于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协作,提高效率。人类社会的演进,也是在寻求一种新的体制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势必会出现对体制的皈依和反抗,这两者其实都是对效益的一种追求。 而对于体制与民间的定义,每位批评家的用词也不相同。对杨卫来说,在我们谈体制的时候,或者在知识共同体的范畴当中,还有一个更大的体制在外围,无形地把大家保卫在一起。 孙振华对体制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广义的体制,即人类都在体制过程中;另一种是狭义的体制,就是既定的、官方的、与民间对立的存在。
对于存在于体制和民间相互体系当中的策展,段君强调激进的策展,但反对过于激进的策展。要在尊重艺术家的基础上,强调策展的创造性,反对把艺术家作品当作一种材料,甚至反对策展人直接介入艺术家的创作,要在艺术产出世界里面,体现艺术作品的重要性。
对于体制与当代艺术的关系,盛葳比较认同乔治•迪基的观点,当代艺术是跟体制合作的艺术,并不是反抗体制的艺术,如果没有体制就没有当代艺术。当前,展览与策展已经在新的实践当中被观念化、对象化,要把策展当成一种艺术创作,一件作品来看待。 王萌则认为我们今天依然没有脱离体制化,很多艺术虽然希望反抗体制,但实际上进入体制是必然的结果。与此同时,(展览)作为策展人的作品,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因此就需要完善的体制对其进行捍卫和保护。 樊林结合自己的策展项目,认为可以把既有展览模式稍做改变,让受众参与介入其中,为发现和理解艺术带来更多可能性。 佟玉洁谈到数字时代为策展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在当下这个时代,网络展览已成为公立美术馆和民营美术馆的一个补充形式,加强数字化私人美术馆建制在当下就显得非常重要,因为它已具备以下四个特征:第一,社会赋权;第二,政治赋权;第三,技术赋权;第四,资本赋权。 孙振华认为当代艺术是制度型的艺术,一个艺术家的成功,离不开策展机制、传播机制、收藏机制等因素的影响。随后,他又举了四个展览作为案例,认为走出美术馆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今天我们还是在过多地谈论美术馆,真正的艺术应该在生活中活跃。 在杨小彦看来,如果我们坚定真正的民间立场,也许美术馆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陈孝信认为“中国远远没有进入美术馆时代。”从当前中国艺术场馆的数量和硬件角度来说,中国已经进入美术馆时代,但也只是一只脚进入。因为现在的场馆“以人立馆”的现象太普遍,而“以规制立馆”这一步中国还没有真正跑出去,又有人又有规制立馆更是遥遥无期。 范晓楠对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多“鬼博物馆”这一奇怪现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中国美术馆建制是国家的制度,落地到地方上其实就与民间发生对话和冲突。” 在泛策展人、泛美术馆时代,是否有一些机遇和可能性是策展人可以做的? 艾蕾尔觉得现在需要建立策展评价机制,并提出了三种方式:第一,关于展览或者批评文章的写作。第二,关于策展档案的历史性记录。第三,媒体平台关于展览的排行榜或推荐。我们评价展览价值,可以从合作的美术馆、策展人身份,以及观众影响力等方面来评估。“
我们不仅要关注策展本身,同时也要保卫策展人。” 2000年之后,随着大型艺术机构的出现,朱青生越来越多地感觉到,这些机构具有很强的话语权,换句话说,策展人实际上是为它们服务的,“目前策展人只作为一个展览或者艺术家的参考数据来把握。” 陈孝信结合他最近10多年的策展经历,特别指出,在今天中国的语境下,策展人的实践,与美术史的书写有一种深层次的联系。
B/机构:公立与民营
第二个分议题为“机构:公立与民营”,所探讨的是公立与民营机构不同的体制背景和发展取向。 中央美院美术馆副馆长王春辰谨慎地分析了美术馆在今天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后全球时代,各大艺术机构纷纷举办大型展览,以期发挥美术馆在公众和公共之间对话交流的作用。与此同时,这些新兴的网红展览和创作,能否构成今天当代艺术的另外一种发展趋势? 既有公立美术馆经验,又在私营美术馆任职的鲁虹,结合自己几十年的经验,真正地感到希望在民间,但要有两个前提,一是经费要有保证,二是老板要有情怀,有实力没情怀这事做不好。 王璜生以广东美术馆和广东时代美术馆为例,向大家展示了官方美术馆与民营美术馆合作双赢的可能性,“民营有民营的长处,但也有短板;公立有公立的难度,但也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如果公立和民营能够合作,各自发挥所长,无论公立还是民营,都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广东美术馆三年展品牌创出以后,王绍强接任馆长,并认识到馆长在其中的重要性。除在重新启动广三展、影像双年展外,未来美术馆将与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进行联动合作,为大家呈现珠三角的另一种活跃态势。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副馆长陈晓阳,从学院美术馆的角度,提出了公立美术馆的发展方向,一、为公众提供文化产品;二、继续加强在馆藏和研究方面的优势;三、把一些反体制的力量体制化,从而实现优化体制的效果。 经常和美术馆打交道的资深策展人陈默,对当前中国美术馆的乱象提出了一些建议。公立美术馆在展示、收藏、学术、教育等方面,多有不足,应该真正的公立起来;民营美术馆中,那些滥竽充数,名为美术馆,实为搞经营的机构,应该有更清晰的定位。 与鲁虹所认为的希望在民间不同,吴永强认为希望还是在公立。民间美术馆因为没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很难有系统的收藏,所以大多数 民间美术馆其实没收藏,只是一个展览的空间。 葛秀支以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为例,提出了综合类大学博物馆的主要功能之一,即为学子提供一个美育的课堂,并通过培养他们的审美建立艺术生态的重要一环,并达到反哺美术馆的效果。此外,博物馆还会加强与周边社区和其它区域艺术机构的合作。 策展人和个人情怀对美术馆的意义,邱敏有不同的看法。如果美术馆有固定策展人,同时策展人的理念与艺术生态系统又呈脱离状态,则不利于美术馆的发展和中国艺术生态的良性循环。此外,美术馆的发展不是靠情怀来推动的,情怀有时就是一己之力,需要美术馆、公众、乃至学术机构共谋才行。 李林则认为,虽然公立美术馆和民营美术馆的目标一致,但两者之间既然存在公立和民营之分,在职能或者功能上, 是否应该避免同质化? 王秋凡以美术馆的功能作为切入点,认为当前的美术馆功能过于单一,要更加细化和有所延伸,所以在美术馆建设方面,应满足各类观众的需求,并最终使美术馆真正镶嵌到居民生活里。 在颜勇看来,美术馆的场域中,存在着三方力量,即体制本身、学术共同体和公众。随着时代的发展,公众在场域中越来越能够表达自我,并改造既定的规则,他们的力量甚至比学术共同体更大,那么公众所发出声音真的代表他们自己的声音吗?会不会是某种东西的伪装? 张光华也认为,美术馆的希望不一定要在民间,因为每年国家会把大量的行政拨款投入博物馆、美术馆等官方机构,这一点比起民营美术馆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关键还是应该看管理者的行政管理能力和策略是怎么样的,这个相当的重要。 沈森认为当前一些标杆性的艺术机构正在丧失自己的学术品牌意识,这是非常严重的议题。近年来,可能是尝到了网红时代的红利,众多机构纷纷举办网红展,从营销策略上来讲,这是很成功的,但从美术馆的学术运营角度,今天的美术馆能够给大众提供什么?仅仅是一个网红留影墙吗?这是应该去讨论的话题。


2019第十三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分组讨论现场/C组
10日上午,三个小组的召集人何桂彦、冀少峰、游江分别对小组的讨论做了综述,产生了一系列富有学术价值的理论和观点,在理论框架上为艺术批评与艺术机构之间的合作提供了新的思考。
年会最后,秘书长杨卫做总结,宣布2020•第十四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将在江苏宜兴举行,轮值主席将由学术委员冀少峰担任。